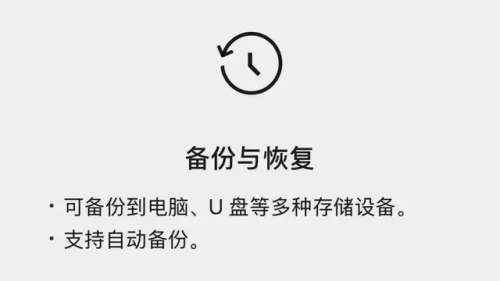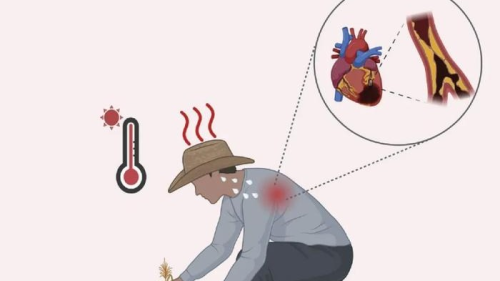活在“老新疆”记忆中的马桥城
字体:
A+ A. A-中国昌吉网(记者 李云辉 文/图)尽管那条曾经洪波涌流的河道已经干枯,尽管河岸边的那座土城已经成为断壁残垣,成为一座“故城”——死去的城,但它仍然活在当地“老新疆”人的记忆中。这座土城就是位于呼图壁县城西北部约90公里处的马桥城。
马桥城承载着“老新疆”人的苦难,也记载着他们用鲜血、眼泪、汗水凝成的一段自强不息的命运抗争史。
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经历了一场劫难。一些宗教极端分子、民族分裂势力煽动民族仇视,制造宗教狂热,滥杀无辜。为了躲避杀戮,难民扛着装满籽种的枕头、口袋,伛偻提携,仓皇逃生。据当地老人回忆,如今在呼图壁、昌吉的苦沟、沙枣园子、老龙河等地,还残存着当年难民逃难栖居过的地窝子和开荒种田引水的渠道、田埂。
为了自保,各地民团纷纷出现。这个时候,芳草湖出现了一个草莽英雄——“豪豪”高四。
高四名克武,因排行老四,故被称为高四爷。高四出生在呼图壁蘑菇湖(今芳草湖总场二分场),早年习武,是芳草湖一带的一名绿林好汉。面对混乱的局面,高四与当地有名望的李长寿、徐大旗、何世海等人联合,聚集数百青壮年组成自卫团,开始保护家园的战斗。无家可依的汉民纷纷从四面八方投奔到高四的民团。为了安置这些难民,进行长久的抵抗,高四等首领决定在呼图壁河与洛克伦河两河下游交汇处修建一座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这座城破土动工,这就是马桥城。
早就听呼图壁的老户讲述马桥城的故事,一直没有机会去踏访。2020年4月底的一天下午,我们从呼图壁县城驱车出发,去踏访那座已经“死”去150多年的故城。顺着呼芳公路北行,沿途田畴弥望,平整如棋枰。行驶到芳草湖总场后继续西北行约50公里到106团团部,按照导航提示又行驶约5公里,来到了洛克伦河与呼图壁河交汇处。这里就是马桥城的所在地。
马桥城实际上有两座城——北城和南城,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城池布局修筑。南城是难民首先修建的,据老户转述和后人踏勘,南城南北长380米,东西宽340米,城墙高3米余,厚2.7米,护城河宽3米、深约1.5米。我们看到,经历了150年风雨的侵蚀,夯土版筑的四周土城墙,虽然有的地方已经坍塌,但是还基本完整,有的地方残存城墙有两米高,而且有的地方还能看出敌楼的轮廓;环绕城墙的护城河长满了红柳、梭梭与胡杨,但仍能体验到当年防护的森严。
我从东城墙的一个大豁口(东门)进入南城,炙热的太阳烘烤着干涸的土地,没有一丝风,闷热的天气让鸟儿都躲得不见踪影。城内已经找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屋,只有那些断壁残垣掩映在胡杨、红柳、梭梭丛中,偶尔能从城中发现一些铁锅的碎屑、牛骨或者猪骨。
一条东西方向的深沟将南城分为南北两部分,这条深沟目测宽约10米、深约5米,这就是当年的洛克伦河,如今河沟早已干涸,但草树茂密。这条河既是城池的屏障,又为难民提供生活用水。为了便于人马往来,难民们就地取材,用胡杨等架起了一座木制桥梁,仅供一人一马通行,这座桥因而得名马桥。如今这座桥已荡然无存,但是桥名却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而且这条河也被人称为马桥河,这座城也被称为马桥城了。
我穿过草木丛,走到了这条河谷中。据说,为了保护城池不受河水冲刷,人们用梭梭筑堤,经观察发现,河流两岸采用了很厚的黏土保护,但是没有发现梭梭筑堤的痕迹。
爬上南河岸,来到城的南部,这里同样是断壁残垣。依靠南城墙有一排保存较整齐的房屋墙壁,但这不是当年难民的房屋,知情者说,这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军垦战士再次到这里屯垦时,在这里建的临时校舍。由此联想到,当年避居在这里的难民们,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没有忘记教育,他们从难民中挑选有文化的人办起了学堂,马桥城里有了朗朗读书声,据说战乱结束后,这些返回家园的孩子有的还考上了举人。

2021年5月,记者在马桥故城拍到景象。
我从西门出来,来到了距离南城西北角四五十米远的北城。有人把北城叫兵城、南城叫民城。这不一定有道理,其实当时这些难民战耕结合,敌人来犯时,青壮年就是勇猛的战士,拿上兵器、农具与敌人厮杀;敌人撤退了,他们就是地道的农民。
既然有了南城,为什么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又修了北城?因为周边形势越来越严峻,外来侵略者浩汗国军官阿古柏率领野兽一样的军队正在从南疆向北疆进犯,在生命财产再次受到威胁的时刻,除了呼图壁的居民外,玛纳斯、昌吉、乌鲁木齐、米泉等天山北坡的居民纷纷到马桥城避难。同时,活跃在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一带,民团首领徐学功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便于和玛纳斯、呼图壁等地民团的联系,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高四早有联系的徐学功带领义军也来到了马桥城。
这个时候,逃奔到马桥城的难民已经有3000人左右,原有的南城已经容纳不下,于是徐学功、高四等头领决定在南城北侧再修一座城。这就是马桥北城。
北城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0米,城墙高约4米、厚2米,城墙四周同样被护城河环绕。我来到北城,看到北城现存城墙比南城完整,城内同样是断壁残垣、同样长满梭梭等,但密集的房屋布局轮廓比南城明显。
经观察,马桥城址在河道拐弯处。难民在这里筑城有好多有利条件,充足的水源既为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保证,又是护卫城池的天然屏障。同时,周边茂密的红柳、梭梭、胡杨可以提供做饭、取暖的燃料。
为了防止河水冲刷,难民们用大量梭梭将穿城而过的河道两岸用土木结构筑起坚固的河堤,然后修筑城墙,第一座城大约历时一年建成。当时人们将这个荒滩中崛起的城称之为“梭梭城”。

2021年5月,寂静的马桥故城。
刚到马桥城的前一两年,难民因为缺乏食物,营养不良,疾病流行,许多人死亡。为了活下去,他们去寻找能果腹的野菜、野草,荒滩中的曲曲菜成为他们活命的救命菜,他们又到河湾里抓鱼,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民间传说“当年的马桥子是吃曲曲菜打起来的”。
马桥城处在呼图壁河、洛克伦河下游冲积扇上,土地松软肥沃,光照充足。难民们逃离家园时用枕头带来数量有限的粮食、马料。他们舍不得吃,将籽种撒在松软的土地上,然后马拉着梭梭柴来回跑几趟,种子就被掩埋,不久绿油油的庄稼苗就长出来了。充沛水源的浇灌,充足的光照,不用施肥,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之后开垦面积越来越大,不仅保证了3000多难民的生存,而且还接济了周边的难民,并为进疆平叛的清军提供军粮。
随着城池的不断完善,开垦面积的扩大以及徐学功民团的入驻,马桥城不仅成为难民的庇护所,也成为北疆抗击侵略军的坚强据点。徐学功、高四等一边与玛纳斯民团首领赵兴体、吉木萨尔民团首领孔才等互相策应,一边与阿尔泰、塔城的武装联系,共同抗击入侵者。
马桥城的难民们一边耕作一边备战,他们不仅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而且也是在守卫疆土。他们身处重围,一点不敢懈怠。平时不论白天晚上,马桥城外的红柳丛中、胡杨林中都有他们的暗哨,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发出警报,难民、民团立刻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徐学功、高四在坚守的同时,不断出击,给盘踞在玛纳斯、呼图壁、昌吉、乌鲁木齐、米泉等地的叛军、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仅在同治十二年,徐学功部在沙枣园(兵团第六师一0五团七连)就与阿古柏部队激战多次,沉重打击了阿古柏侵略军,并缴获了阿古柏刻有俄文字母的指挥刀。
就在徐学功等人艰苦抵抗时,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军西征陕甘、新疆。1876年6月11日(光绪二年五月二十日),左宗棠属下刘锦棠部抵达吉木萨尔。徐学功、孔才等民团与清政府西征军大力配合,清军势如破竹。8月18日,清军收复乌鲁木齐。接着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相继光复,到1876年11月,北疆的阿古柏据点全部拔除。1878年1月(清光绪三年十二月),驱逐阿古柏战役胜利结束。
阜康、米泉、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相继光复后,难民们陆续离开马桥城,开始返回已经荒芜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大约生活了13年,许多孩子都是在马桥城出生,根本不知道父母魂牵梦萦的家到底是什么模样。
劫后余生的难民们回来了,映入眼帘的是断壁残垣、萋萋荒草。据《呼图壁乡土志》记载,光绪三年三月,“呼城鞠为茂草”,“城垣瓦砾,书役无存,遗黎不满十户”。
从光绪三年到六年,呼图壁一带“蝗旱频仍”,返回家园的难民既无耕牛,又缺籽种,“皆饥困不自存”,新上任的地方官吏带领农民“驱蝗赈发牛籽,豁免额征,开渠设塾”,“丈地垦荒”,“民命始甦(苏)”。
大约到1879年,马桥城的难民都已经全部离开。随着上游土地开垦面积的扩大,用水量不断增加,下游的马桥河水量逐渐减少,到1958年,上游的大海子水库修建后,马桥河就干枯了。
一个半世纪后,我肃立在马桥故城城墙。西北望,不远处是高地起伏的沙丘、连绵不绝的梭梭、红柳,这就是北沙窝道,可以到达阿勒泰;东南望,整齐的农田如巨大的棋盘延伸到天际,不远处,楼房林立,屋舍俨然,那是106团的团部所在地。
回到呼图壁县城已经是黄昏,当年难民们用了13年的时间才回到家园的路程,我们历时不到两个小时。夕阳中的呼图壁县城弥漫着海棠花、沙枣花的花香,处在春光澹宕、香气氤氲的氛围里,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150年前那些难民逃亡路上的绝望神情……
马桥城虽已故去,但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民族分裂是各族人民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