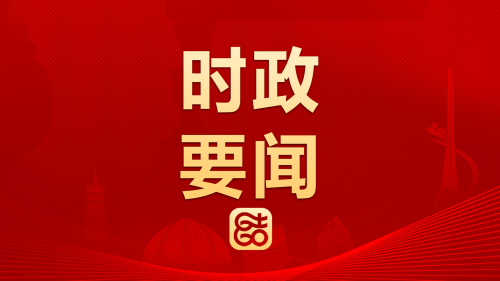《我的西部故事:
在黄蒿湾村找到人生的另一道算式》
我叫谢映兰,来自安徽,一个金融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或许你很难想象,如今的我会在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三台镇黄蒿湾村的村委会里,抱着一摞惠民政策手册走家串户,在羊圈旁调解邻里纠纷,甚至举着手机给老乡拍短视频。是的,我的工作与财务报表、概率模型毫无关联,但在这里,我找到了人生的另一道“算式”——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换得信任。
为什么是新疆?
第一次知道新疆,是因为大学室友转发的一条视频:“不来一趟赛里木湖,你就白活了!”镜头里湛蓝的湖水和远处的雪山像一块磁石,瞬间吸走了我这个南方姑娘的心。填报志愿时,我瞒着父母把“新疆的大学”塞进了志愿表,直到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妈还反复确认:“这学校不是搞传销的吧?”
在新疆读书的四年,我几乎走遍了北疆的草原和湖泊。毕业后,当同学们纷纷挤向一线城市投行、证券所时,我却发现自己的心早已被这片土地拴住了——这里的风是甜的,天是透亮的,馕坑里飘出的炭火香比任何香水都踏实。我说:“我还想去南疆看看。”于是,我报名了西部计划。面试时,我激动地解释:“我想去最远的地方,做最实在的事。”可分配结果下来时,我被留在了北疆,岗位是吉木萨尔县三台镇黄蒿湾村的乡村治理专项志愿者。
村里有什么?
初到黄蒿湾那天,副镇长开着一辆小汽车来接我。车窗外是大片绿油油的草原,远处成群的牛羊像撒在绿毯上的珍珠,村口的树下,几个裹着头巾的阿姨正踮脚张望。村支书笑呵呵地说:“小谢,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
很多人问我:“在村里能干什么?”我的回答总带着骄傲:这里有课本里学不到的“三堂课”。
第一课是“泥土数学”。作为金融数学专业的学生,我曾以为自己的优势是算数据、理账目,可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村里的大叔不会用Excel,但能精准报出家里30只羊的出生日期;哈萨克族大姐不懂微积分,却能通过草场的长势算出够不够牛羊过冬。我收起笔记本电脑,换上运动鞋,跟着村干部学“土办法”:在炕头用瓜子记账,用树枝在地上画调解流程图,甚至从羊粪蛋的干湿程度判断牧民的收入情况。
第二课是“人情经济学”。夏季入户走访时,村民总会把刚摘的葡萄、杏子塞满我的口袋。寒冬腊月,刚掀开某户人家的门帘,热腾腾的奶茶和手抓肉就端了上来。起初我不好意思“白吃白喝”,村主任却提醒我:“你推辞,他们反倒难过,这是把你当自己人。”后来我学会了“等价交换”——给小学生辅导功课换一顿拉条子,用手机银行帮牧民查补贴到账,换来一把还沾着露水的野花。
第三课最珍贵,叫“信任的重量”。去年冬天,村民马大哥和邻居因草场界限吵得不可开交。我捧着《土地承包法》上门调解,却被一句“丫头,你还没我家巴郎子大呢!”噎得满脸通红。后来我索性搬个小板凳,坐在他家羊圈旁算账:“您家去年卖羊挣了8万元,要是打官司耽误接羔,至少亏2万元……”当他终于签下调解协议时,我突然懂了:在村里,信任不是靠学历换来的,而是用一道道泥脚印夯实的。
我的“不专业”与“大作用”
到村里时,看着其他到村大学生熟练地填表格、写材料,我总觉得自己像个笨手笨脚的外来户。金融数学课上那些复杂的公式,在这里连牛羊的数目都算不清——毕竟村民从不用笔记,却能闭着眼说出自家三十只羊每只的耳朵特征。
转机出现在去年冬天。
渐渐地,我发现那些看似无用的专业知识,其实像盐巴撒进奶茶——看不见,但能让生活更有滋味。走访独居老人时,我把他们的需求记成表格:王奶奶想要每月理一次发,李爷爷需要代买降压药。当我把这些“数据”按月统计给村委会,现在村里定期有流动理发车,卫生所的大夫也会背着药箱上门了。
现在的我早就不纠结专业对不对口了。帮村民调解草场纠纷时,我教他们用手机计算器算损失;组织妇女学国家通用语言时,我把金融课上的逻辑思维训练改成“看图说话”游戏。村支书常说:“小谢的脑袋像转经筒,晃一晃就有新点子。”而我知道,真正的学问不在书本里,而在老乡递过来的那碗滚烫的奶茶中。
如今的我,手机相册里全是“不务正业”的证据:和村民拍的段子,在帐篷里教孩子写汉字,举着灭火器带民兵演练,教维吾尔族的大人读汉语……常有朋友问我:“整天忙这些琐事,不觉得虚度光阴吗?”我总会笑着点开相册里那张照片,看着照片想起我当时做那些事的骄傲感和幸福感。比起城里面的高楼,这里的蓝天白云下,藏着更滚烫的人生价值。
星空与初心
记得某个加班的深夜,我独自走回宿舍。一抬头,漫天繁星像打翻的钻石匣子,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冬不拉琴声。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四年前坐在教室里刷高数题的自己——那时的我以为,人生的答案只能在公式和代码里寻找。而现在,黄蒿湾村的每一声“丫头”、每一张笑脸、每一句“共产党佳克斯”(哈萨克语:好),都在告诉我: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这片土地给我的,远比我能付出的更多……
谢映兰
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