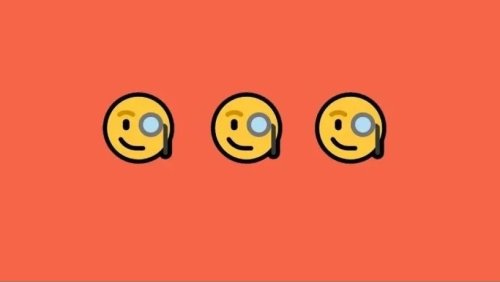北庭都护府“悲田寺”消失千余年重返世间
字体:
A+ A. A-丝路昌吉/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记者 左武银 许乐
“这就是北庭故城遗址内发掘的‘悲田寺’刻字陶器残片,今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移交给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展出。”今年夏天,在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展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新疆队队长,北庭故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郭物向记者介绍“悲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出土经过。

拼接的“悲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内侧底部。记者许乐 摄
北庭故城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城正北12公里处,是我国唐代至元代新疆天山以北的行政中心城市遗址,曾为丝绸之路北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它见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理,以及中华大家庭里各民族从未间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家数次集中对北庭故城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北庭故城遗址于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2月,入选国家重要大遗址清单。

北庭故城遗址。记者马乾 摄
郭物介绍,2021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庭学研究院组成的北庭故城考古队,在北庭故城11号遗址中发现了几块陶器底部残片,内侧刻有汉字,经考古工作人员现场拼对,确认为“悲田寺”3个汉字。由此,这座湮没于地下上千年、在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的北庭都护府的“悲田寺”,浮现出重要线索,重新回到世人视野。
11号遗址位于北庭故城子城西南部,面积约为1200平方米,是高于周围的一个台地。台地南部现在还残存一道夯筑的围墙,遗址已经被严重破坏,大部分区域暴露出原生土,台地及周边被挖了不少坑和井。这些坑深5米至6米,井深7米至8米,从这些坑和井里出土了大量残破的瓦片、砖块和陶片,大多是这个遗址原来的建筑构件和器物。郭物说:“别看陶片破破烂烂的,但是它刻了字,所以我们认为非常重要。而且出土于北庭城的核心区,位置相当于紫禁城的武英殿(清初武英殿被用做皇帝理政便殿)。我们一开始认为是官署遗址,没想到西南部的院落是座寺院。”

北庭故城11号遗址。受访者供图
随后,考古队在清理过程中又发现两块残片,但只剩“悲”字,且大小不一、写法有所区别,但可判断出3件不同陶器残片均刻有“悲田寺”字样。郭物据此推测11号遗址的院落就是“悲田寺”所在地。
“悲田”一词源于佛教,是佛教福田思想下的一个概念。据《资治通鉴》卷241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养,官以本钱收利给之。”在《唐会要》卷49《病坊》中也有相关记载:“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宰相李德裕奏称:‘恤贫宽疾,著于周典,无告常馁,存于王制,国朝立悲田养病,置使专知……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

拼接的“悲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外侧底部。记者许乐 摄
郭物介绍,武则天长安年间设立的“悲田养病坊”,由国家出钱、寺庙负责经营,官督寺办,是半官半民的疗养所,最初主要收容病人;后来扩展到救济贫困、疗养疾病、施药、抚慰孤独等功能。此类机构先在长安和洛阳开办,后逐渐推广至全国。
在郭物看来,“悲田寺”刻字陶片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即使在边疆地区,唐代的社会治理体系也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悲田寺”被置于北庭城最重要的子城内部,这一布局充分体现了武周和大唐在国力强大时,无论是在都城还是边疆,均通过国家力量,对社会中孤老贫病等极弱势人群的帮扶。这既反映了佛教福田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充实与影响,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追求小康社会与天下大同理想的深刻体现。
“唐代政令畅通,它的律令可直达州县,驿道系统覆盖全国。所以你看长安城有什么东西,北庭城就有什么东西。‘悲田寺’的存在,以及这里建筑形式和出土的瓦当等器物跟长安城的西明寺、青龙寺出土器物高度一致。这种现象表明,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在唐王朝统治下,尽管全国各地存在地域差异,但在关键领域仍呈现全国一体化特征,这是今天我们中国能那么团结的一个基础。”郭物评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