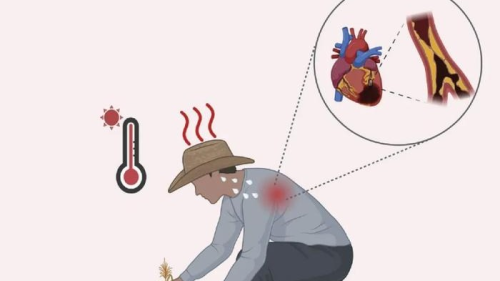梦回木垒
字体:
A+ A. A-□朱胜勇
昨夜,我在梦中回到了三年援疆的第二故乡——木垒,而且一晚上都在梦中的木垒徜徉,直到晨光唤我醒来。从去年五月援疆期满结束返回南平到现在,十个月过去了,不管想或不想,念或不念,似乎木垒都在那儿,在心中一隅,但却始终都没有梦到,有时也有些失落,想着是否自己对木垒的情不够深,意不够浓。
梦中是从南平穿回木垒的,不是乘飞机,也不是乘高铁,似时光穿梭一般。梦中迷迷糊糊的,前一秒还在南平在云谷,下一秒就穿越了时空,穿过两地数千公里的距离,到了木垒。
梦回木垒,映入眼帘的不是一望无际的充满生机和绿意的万亩旱田,不是蓝色勿忘我点缀其间的马圈湾,不是县城宽阔的大道、上班的政府机关、援友一起工作生活的援疆分指挥部,不是“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历经沧桑的木垒胡杨,不是甘甜的天山雪水流淌其间的草原坎儿井,也没有看到满是纯净的木垒天空蓝。
梦里,天上云层密布,不久竟然下起了雨,还是哗哗大雨。要知道,雨对常年干旱的木垒来说真的是贵如油呀!梦中的我禁不住拿起手机,对着倾盆大雨拍照,我要让生活在四季有雨的南平同事们,看看这木垒难得一见的雨景。
迷迷糊糊中,我又来到了万亩旱田。可是,这梦中的万亩旱田,此时不是生长着绿油油的旱地小麦,不是结着饱满豆荚的鹰嘴豆,却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正在拔节的水稻,阵阵微风吹过,稻浪飘香沁人。我纳闷着,水稻怎么会生长在旱地的缓坡上呢?应该是水稻种植技术提高,旱稻推广到木垒了吧?往旱田的左边望去,一片冬翻后没有种植稻麦的旱田里生长着菟丝子、葛藤,还有好些野树莓,小朋友们在其间奔走、嬉戏、采树莓。
梦中的我来到了英格堡乡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到了木垒书院,到了新疆作协主席、木垒书院院长刘亮程老师家中。不是到他满墙是书的书房,不是到他的会客茶室,也不在那座石碑孔子像下,却是到了一张满座的大圆餐桌边。因为到木垒援疆的缘故,我有幸认识了刘亮程老师,去年援疆结束即将返回之际,我还敬请刘老师赐以墨宝,他欣然答应为我送上了朱子语类中的“持敬致知”四字,而此时梦中的我,看到的是一张大圆桌,刘老师端坐其上,爱好文学的木垒青年围坐一圈,桌上没有拉条子、手抓肉、大盘鸡、三粮糜子酒,而是一杯奶茶,刘老师逸兴遄飞、风趣幽默,用他那思接千载、纵横万里,又充满哲理、引人入胜的生动话语,向青年才俊们讲述本巴国度的故事,让大家从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故事中,思考世界的本真。
正当我沉浸于刘亮程老师的本巴世界之中时,一个声音突然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周金德主席,你网购的康德哲学书到啦!”于是,我又四下找寻周金德同志的身影,没有找到他人,但朦胧中又勾起我对他的回忆。我初到木垒工作时,周金德同志是县政府办主任兼信访局局长,后来提任县政协副主席。早年凭着一股韧劲取得法律从业资格,他法律业务娴熟,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是处理信访问题的好手。我是在一次信访日接访和他打下了工作交道,之后我又因为包联一个较难化解的信访案,多次请他帮助梳理信访案的来龙去脉,探讨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化解对策。后来,这个信访案得到了妥善化解,我和金德同志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相互欣赏。援疆三年多,我深深感受到木垒当地干部守边护疆的家国情怀,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抓铁有痕的工作韧劲,坚定坚决的工作执行力,以及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金德同志称得上是木垒当地干部的一个缩影。
一夜的木垒行让我略带疲倦。我躺在床上回忆梦境,回想木垒。是的,平时没有刻意去回想木垒,也没有渴望梦中回到木垒,昨天夜晚还是在不经意中就回去了。这时我回想起,每当月色如洗的夜晚,在木垒的广场散步时,望着树梢上升起的天山明月,我就想着南平的这轮圆月也升起了吧;而今夜幕时分从办公室回到小区,漫步云谷步道望着当空的皓月,我又想着木垒树梢上悬挂着的那轮天山明月,此时是不是也正倾洒着她的淡淡清辉。木垒之月与武夷之月,虽是两地,却在一心。心在,木垒在武夷在;心在,武夷木垒皆故乡。
此时,我好像真的从木垒的梦中醒来了!
(作者系福建省第八批援疆干部,曾任木垒县委副书记、福建援疆南平分指挥部指挥长;现任福建省南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